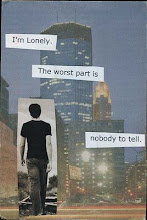這幾天都是看見王心凌在《乘風破浪》斷層出圈、屠榜等的新聞與議論,還有視頻。中國網友的留言很多都是金句,剛讀到的是很有意思:「初見斜瀏海,再見地中海」,說穿了就是懷舊心態推動而已,憶起昔日青春的年少,而人到中年後成了中產有妻有兒,或是生活壓力山大,而需這些甜姐姐勾起回憶舒緩一下自己現實生活的苦。
我其實沒有真正關注過王心凌,對我而言,她不屬於美女,特別是一張鴨形嘴太過矚目。只是我記得很多年前我的一位很宅男的直男男同事,寡言又怪僻,有次無意中提到原來他喜歡王心凌,當時他的神情是那種遙望迷醉的光彩,但我那時很不可思議地望著他,怎麼像這樣asexual的男人,看來是高知的人群也會這麼膚淺地迷戀一個芭比娃娃似的醜女人?
其實一如昨天我在這篇文章說的,2000年代是我的成年人職場生涯的序章,那時放太多精力在職技的提升,除了脫離香港流行曲,我連台灣的華語歌也放棄了。
而且,我向來對女生的歌聲不是很欣賞,除非是巨肺歌喉,所以像蔡依林、王心凌、蕭亞軒或是張韶涵這一類是無感。
她們若是靠賣相與身材,我不是直男,是絕緣體,如果靠歌藝而只是在台上蹦蹦跳跳,那種甜膩會讓人反胃。這情況就與當時的Twins火紅的情況一樣,這些傻白甜的甜姐兒的形象,其實是符合了宅男腐化的女性形象,認為女性就是應該這種甜甜嗲嗲,其實也是一種性幻想的投射。
所以我看到中國網友有人留言指稱在小學時常聽到王心凌,就會心一笑的,當年我是以成年人的視角看到她唱著那些什麼「愛你」的糖果歌時,就如同聽兒歌。
而當年在聽兒歌的兒童,現在長大了,他們覺得很回味,懷念的只是當年無憂無邪的純真歲月,王心凌免費出現在電視/手機屏幕為他們載歌載舞,而且還是體態曼妙如同少艾般,只是一個情感的催化器。
其實這讓我想起《乘風破浪的姐姐》裡的陳松伶,在一公後後就被刷下來了。陳松伶當年也是窈窕淑女,但後來因病後才暴肥得如此不堪,輸在顏值和體態上。當然,陳松伶也是成名較早,所以也與現時代脫節蠻久了。
而王心凌轉眼就是39歲,其實是姨姨級別了,只是猶幸的還可以有瘦腰等臉部以下的衣著炮製形象,但其實那一張臉,我在她一出鏡時我就嚇倒──她的假睫毛是否掛跌了還是失手畫得太粗了,我看不到任何甜美,我只看到很苦澀。
她出場時,我想起的是第一季另一名同樣甜寵形象出道的金莎(一個聞所未聞的大陸女歌手),當然金莎的名氣與王心凌不能相提並論,但兩人的那種娃娃聲或甜嗲氣質掛帥,就讓我有錯覺,那一刻我就心裡想,王心凌該是很快被刷下來,同時只是做一個陪跑龍套吧?而且,王心凌接下來是否會像金莎一樣,出現在征婚類綜藝?
王心凌當年的走紅,是很成功的流行歌影視的商業操作,是依著既定的模式來定型人設,與一個芭比娃娃無異,造形象就是換上衣服而已。
而當時我看見王心凌以Sailor moon式的校服登上舞台,擺弄著裝甜的舞姿時,側著臉嘟起小嘴,扭著腰翹起小腰,還有兩手不斷凌空划圈時,歌聲還是刻意低壓脆脆的模仿少女,我是感覺到有些悲哀的,39歲了,還要做甜心,而且她矢志80歲也得做甜心奶奶,人到白頭還得依著群眾的喜愛定型來活著。這樣的人生,是沒有自主的。當然,這樣的事業生涯,也可以換取她餘生的「榮華嬌貴」,只是有事業,但沒有靈魂的人生。
像幾天前看的《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這部戲,我也是一邊想,楊紫瓊真的是過氣了,楊紫瓊在戲外受訪時感歎中年女演員已拿不到劇本了。而她也不惜放下昔日的身段拍這麼荒謬的電影了,女歌手、女演員一過氣,還剩一口氣,就是白頭宮女的悲涼了。
相對之下,許茹芸在初演時不唱成名曲《如果雲知道》,而改唱後期專輯一首較冷門而曲風陰暗的曲子《現在該怎麼好》,其實就看得出她已拋下包袱,而是想讓大眾看到另一面的她,另一面可能不是那麼討好大眾的技能與才華,但她一意與過往的她割席,是一種走出來的智慧與胆識。
而王心凌在台上扭啊扭的,我記得那一刻我是為她感到悲哀的,悲的是她真的要拄杖做甜心奶奶嗎?這是扭曲的人生歷程啊,哀的是她還是沉醉或是拿不出商業預定人設以外的本領與大招出來,她沒有剩下,她就只有這麼多。
或許這是王心凌的無心插柳,但這樣全網爆紅,而且是觸底反超後命運也不是人人可有的。在商業上,她已成為會生金蛋的母金鵝了,現在綜藝招商或是廣告主要的就是這些頭部。而人到中年的佬,且看你們這批淫佬還要繼續回憶與意淫多久?我可以預見的是,王心凌會跳更多這種甜寵舞,或者會繼續在臉上大刻大雕大注,千刀萬剐一張臉,繼續違逆歲月與地心吸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