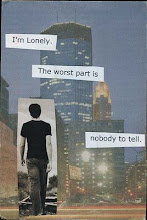第三,是新鮮感。
第四,是金錢考量。
第五,是習慣。進餐的選擇來來去去就是那種模式,而這種模式已形成一種習性,甚至如同天生的左手與右手分工一樣,怎樣都改不了。
那天我又在猶豫著要吃什麼好呢?我兜兜轉轉地在谷中城底樓的食肆裡徘徊,像無主孤魂在遊盪著──有快餐、中餐、可以有豪華的饗宴,也有平民式的熟食。最重要是肯花錢。
到後來不知怎樣地,我突然想到另一個主意:選擇,就在于創新。
我的新方針就是進一間餐館,如果曾經去過的餐館,就點一些不曾點過的菜式。而如果是平時都不想去光顧的餐館,也逼自己去嘗試踏足,看看有什麼可以嘗試一下。
譬如在大人餐廳,平時我只會點其麵食,那麼我一定要挑其他的,如飯菜。另外一些平時不去光顧的,如那些Chicken Rice shop等的「失真」、「偽快餐」式的雞飯店,也可以嚐嚐。
如果每次都挑不同的菜式、進不同的餐館來光顧,每次都是新鮮感,那麼我就不用愁苦無選擇了!
突然間,我覺得我好像變成了一個天才。那一天,我就跑到去The Gardens那檔叫作「士林夜市」(不大確定)的小食肆,然後叫了一碗蚵仔麵線來吃。
而這是我第一次光顧。我想起為何平日我不會光顧,因為我總覺得這些取經外國美食的食肆,只是沾光其名,而作不到原汁原味、地道的料理,其實形同騙人。
(當然,我在嚐了後覺得我的判斷是對的)
但我沒有後悔。因為我覺得我終于對我的「實驗」有了考證結果。那麼是否會有下次再光顧?或許我需要輪迴一圈後,才來「食髓知味」。那可能已是好久的事情了。
後來我想,就是這種先入為主的判斷、這種過于計算的理性思考過程,變成一種無形的枷鎖鎖著我,腳鐐著我的行動,我設定了一個框框來限定著自己,不要越界,不能即興,一切隨著模式走──只有模式,而放棄了形式。
在物理上,有一種原理就是「阻力最小的路」(Path of least resistance),同理于中國人的俗語「水向低流」,即是水流會因地心吸力而往下流,而且不會攀山逆流而止(除了特定的地勢);而電流也是順應最順勢的線路而流通。這種物理表現主要是跳過、繞過障礙物的途徑。
物理上是順勢而走,其實是抄捷徑。而這種物理表現也不是是我們做人、處事時的圭臬嗎?我們會避開正面沖突,在塞車時我們總會挑是否另有途徑來避開等等。
這包括在挑食物時,我往往都會以現有的認知、味蕾的習慣、對食物的份量、營養成份等,甚至是──看看那間食肆的「種族色彩」(例如印裔店的食物往往是紅艷艷的咖哩,但你不能餐餐都挑咖喱。)
因為這些認知反而成為過不了的關、打不開的結,于是每次我就選擇走在阻力最小的路,讓我更快速地做出選擇。
經過重重又重重的過濾後,像隔了渣一樣,就變成寥寥無幾的選擇了。而且失去了意外的驚喜,或是即興的可能性。
那一天後,我覺得我的選擇突然豐富多元起來,對我而言,菜單似是重生一樣新鮮,而且看著餐牌時,我心裡自問的問題是:有什麼菜式我是沒有點過的?
我很快地就找到了答案,即使仍然有許多項菜式我沒嚐過的,但我告訴著自己:就先嚐A,下次有機會再嚐B。還會有下一次,聽起來是綺麗與充滿希望的,而且,這也是對選擇的寬容。
原來當心態不一樣時,視角也會像萬花筒一樣奇幻多姿。當只是用一個角度去論斷「喜歡」與「不喜歡」時,我錯失了很多東西。
那麼之前的我,是否過于拘泥、守舊、固步自封?
●
後來,我向朋友提出這新觀念時,他說:「那麼,這道理會否應用在男人的選擇?」
我有些猶豫,如果只是為求新奇一試不同的男人品味,那我就假設一下情況:我是否會選擇超磅的相撲手來歡愛?或是選擇一個侏儒式的男人來擁抱?
後來我覺得我的新歡念又被推翻了,我說,「不會。男體的選擇是性慾念在作怪,肉體的感官比味蕾與胃口複雜多了──」
看來我還是未看破世情。而且,選擇男人,我還是會怯場,然後選擇同樣的舊路──阻力最小的路…
(下期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