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1、1
↓
1號、0號、1號、1號。
有多少個0號、有多少個1號?不知道,但30個1號和0號都會在這個數字中決一「雌雄」,爭奪當選真正的大馬乳牛。
0號,這個斑駁唇印般的圓形,讓我不禁莞爾,我竟然想不到一本全由女性編輯主導的男人時裝雜誌,竟會創造出如此強烈性意味的「10」字形設計,完全散發出同志不言而喻的性暗示──這個圓形乍看像「菊花眼」。
沒唱后庭花的讀者們,應該不知道什麼是菊花眼吧!

Recent Posts
NIFH最新一屆的猛男比賽「THE Hottest Hunks in Malaysia2006/2007」又來臨了。我還是買了一本來收藏,就為了看裡頭的30頭乳牛如何「擠奶」。
相當意外的我在裡頭看到三個常在健身中心碰見的乳牛,他們也參賽當選手了。一些平時在你身邊換衣褲的人,突然成了一具具身體油光閃閃的雜誌人物,當然有些不期而遇的驚喜。
然后接下來就去檢視他們的肌肉了,還有其他身體部份,例如我的腦海中會突然想:「咦,原來他的乳暈『醬』大的。」之后就越想越歪了。
不過,這些so called猛男裎胸露體,就會招來這樣的聯想,我想其他讀者也是會其他形形色色的聯想。
更叫我好奇的是,這些平日常相見的乳牛,卻在身高上報大數──平時見他們時都比我矮小,怎麼在雜誌上登相片時,就長高了幾十公分?
這些猛男在雜誌裡回答4項問題來自我表現。
第一題是:要成為THE Hottest Hunks in Malaysia,需具備什麼條件?
第二題:你最滿意/欣賞自己身體的哪一部份?為什麼?
第三題:你心目中的理想學習對象/榜樣是…原因?
第四題:請用三個字來形容你自己。
除了看照片,看看這些乳牛怎樣表現自己時,我真的啼笑皆非。
首先,乳牛為自己冠上一個洋名,其中一個叫「Freaky Ng」,我以為是植錯了字,到后來確實真的叫Freaky──他真的很Freaky,哪會有人來用帶著「怪胎」含義來用作自己的名字?或許,我們遲些會看到有人用Silly、Moron作自己的洋名吧?!
這是標新立異,卻成了四不像,真不知所謂?還是他不懂英文?
接著我就去看他們的答案,大多數都說要當大馬乳牛,應該是要具備健碩的身材,這樣的答案只能說切題,但也是望文生意的膚淺答案。
第二條,每隻乳牛自我評估最欣賞的身體部份時,千篇一律的答案都是贊美自己胸肌、手臂等上半身肌肉,最爆笑的是主辦當局要他們解釋為什麼喜歡這些身體部份時,他們不得不老黃賣瓜,自買自誇地顧影自喜。但我必須體諒在這樣的白癡問題下,自戀狂的出現是無可厚非的。
可是,沒有人說,他們欣賞自己的腦袋。我想腦袋也是身體的一部份吧,而且是最重要的一部份。我讀著這些答案時,想起一句老話:「四肢發達,頭腦簡單」。
第三條的答案,30隻乳牛裡幾乎所有人都視另一個男性為理想學習對象/榜樣,只有5隻乳牛有不同的答案,會答稱說他們欣賞他們的母親、阿姨、名模Tyra Bank,還有一個還搬出偉大的上帝,另一個答稱「自己」。
其他的乳牛都崇拜肌肉型的男明星、政治人物或是運動家或是健身教練為理想學習對象,乳牛喜歡乳牛,也是正常的吧!但同性相吸,就有些曖昧了。
至于照片效果,我發覺有些腹肌練得不夠碩實的乳牛,卻被安排坐姿,以致擠出了腰際的贅肉,是吃了暗虧。
這些油光乳牛照片上大致上都是扮酷、扮炫的造型挺身而出,無奈暗透出一種青樓裡的煙視媚行意味,不言而喻的妖嬈治艷。
再看每個人的撩人姿勢,我可以斷定其中90巴仙都是同志幫。我回想起過去幾屆的乳牛比賽,細數一下,原來馬來西亞也有這樣多長得不俗的乳牛同志幫。
我何必去台北找乳牛呢?
●
乳牛比賽如此受落,也反映了社會上的「猛男情意結」(Adonis Complexes)下的影響力,每個人都視有肌肉,有線條才是猛男或型男。這些情意結構成的意識型態,更影響了同志擇偶的心態,以致非猛男的同志,在潛意識裡就失去了尊嚴與自尊。
所以,吉隆坡的健身中心才如此蓬勃發展起來。
到底為什麼乳牛比賽如此受歡迎呢?他們愿意在眾人面前脫衣讓人評頭論足,他們還得在決賽時的派對上成為展覽品一樣地展示肌肉、體膚毛髮,大家得到什麼?
我不知道這些乳牛比賽的社會意義有多大,但是明顯地,這些乳牛比賽包含了商業利益的考量──對雜誌商、廣告商,還有一些一心一意闖出名堂的選手,都是掙錢的機會。
所以,我就用十令吉買了這一本雜誌,太公釣魚,愿者上釣。
這類比賽其實只是要選乳牛,評肌肉,更不是選秀才,或許我的要求太高了──有沒有腦袋與內涵其實並不那麼重要,我只是擔心自己寫了這一大堆文字,真的是「對牛彈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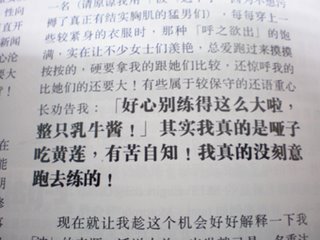
這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我竟然翻到最新一期的NIFH雜誌時,讀到「所謂」著名的電視節目與電台主持人KK WONG(黃國強)的專欄文章《挺挺兩「胸」弟》裡的這一句話:
「好心別得這麼大啦,整隻乳牛醬!」
早前NISHIKI對我說,我所提及「乳牛」論相當紅火了,因為他們都用來形容那些在健身室裡的猛操肌肉的筋肉男當成乳牛。最重要的是,乳牛應該有一爿雄渾的胸肌,胸廓與腹肌分明,而這些乳牛的肌膚通常都乳白色為主,因為他們只在室內操練肌肉,鮮少接觸到陽光,欠缺古銅色的健康膚色。
是的,我與朋友之間也用「乳牛」來稱呼這些肌肉男。至于那些身材超標,或是過于「福泰」的男人們,我就稱他們為「滴油叉燒」。
讀到黃國強提及乳牛的字眼,不知道NIFH的其他讀者是否會明白這裡頭的意義?
否則,他們也想像不到KK與一隻乳牛會有什麼關係。
當然,乳牛是用來「擠奶」的,KK是否真的是乳牛?在我的字典定義裡,還有從平時報章或電視裡看到的KK,我想他還不是乳牛,應該是乳豬吧!因為夠粉潤。
他寫道:「所以我要大聲宣佈,大聲疾呼:『我愛同志!我愛斷背!請繼續討論我吧!』」
我印象中KK像一個「花旦」,他是不是同志?可以是呼之欲出的答案,也可以是心照不宣的認知。不過,這句話夠精彩,是不打自招的雙關話──他沒有承認自己是同志,但也沒有拒絕承認自己是同志。
我突然想起KK以前在電台裡的扮鬼扮馬的整蠱節目,有些懷念呢,雖然我沒有常扭開來收聽,畢竟很久沒有聽到這樣無聊的節目了,讓皮肉笑一笑也是一種運動。
我拿起床頭的一張照片,那是一張多人合照,然后我問裸著身體的他,「你在哪裡?」
他語氣平淡,「你看不到我嗎?」
我仔細地端視那張照片裡的每張臉孔,我才發覺他的存在,那是他的年少臉孔,停留在一個舊時空。
我有些不可置信地看著照片裡的他,不可置信──因為我對這個人如此陌生,而且,我連他現在的樣子長成怎麼樣也不清楚,因此無法從照片裡的臉孔去清楚辨識,關鍵是,他就是那一張大眾臉,那種容易埋沒在眾生譜裡的臉孔,過目即忘。
不可置信地是,我竟然與他上床了,一個長相平凡的男生。
●
長相平凡不是一條罪,我尊重這世界上多元基因的存在。在聊天室裡偶遇佑格時,對他其貌不揚的相貌的確沒有什麼印象,我們聊過了很多次,他一直說我是他喜歡的類型。
後來,約會就醞釀成形了。我沒有特別地在意,我還在嘗試讓自己走出椰漿飯的影子,加上工作忙碌與假期等,所以無法遷就時間去會見佑格。
佑格的手機短訊不斷催問我們何時相見,他越是顯得迫不及待,我越感不安,我總覺得對方若是在聊天室投資過多的希望,最后失望愈大。況且,他只是從照片中看到我的模樣,但口吻間已顯露出示愛的意味了。
這絕對不是一種健康的心態,因為相片始終會帶來盲點──我當然忘不了多少次約了網友出來見面后,對方投向我的第一眼目光完全沒有神采,當然這種約會淪為敷衍了事的酬酢,最后只是「嗨─拜」式地終結,即使之前雙方連性行為喜好都談過了,更部署了下一步可能性的發生。
所以,我要走出盲點,我告訴自己,即使對方其貌不揚,但性格間或許有可取之處,或許可以培養出好感出來。
所以,我們見面了。
●
我和佑格相約了一起吃晚餐,我不抱持任何希望去赴約,也不想偽裝什麼了,就如與老朋友一般地表現最自然的一面出來就好了。
我問他:我與你想像中、和照片中的樣子,是否有什麼不同?
他淡淡地笑了一笑,沒有差別。
現實中的佑格,與相片中的形象還是有差別,我應該怎樣形容呢?──就如同韓國的天皇巨星Rain一樣,但是一個沒有肌肉、舞技、歌喉的Rain,你需要非常仔細地去發掘他的魅力。佑格就彷如未成名前的Rain一樣。
所以,我就從他的談吐、識見等尋找加分項目了。但是他比我還年輕,勝在年輕與有明亮的未來,但他也是一個文靜含蓄的人,他與我分享他的出國經驗,不過當我問到該些國家的首都與文化情況,佑格搖搖頭,答不上來。
我問他是否有到三溫暖等的地方,他說,他沒有那般「放」放蕩,還是開放?。好一個乖乖牌。
全晚的談話局勢幾乎由我主導了。到最后我也有些累了,提出先行結束晚餐的要求。
他過后寄了幾則短訊給我,正式宣示他對我有感覺,探問我們是否有可能發展下去,我有些受寵若驚,然后他開始寫「想我」類似的話了。
佑格還寫說,他本來要我隨他一起回家,他說他自己獨居一房…我在奇怪,他不是聲稱自己沒有那般「放」嗎?
●
后來,我決定讓自己試一試。可是我真的沒有太多時間去與他約會、看戲或吃飯,我不想下一次約會只是我一個人在說話,而到最后,我想佑格還是會問我:你要不要上我的家?
所以,何不索性上床,那樣就可以透徹地進一步了解對方,省去了雙方的資源成本。
所以,我們第二次約會時,我是去他的家。
我望著他凌亂的房間,有些訝然。那是一個十分窄小的賃居房子。他開了幾張大馬旅台歌手的唱片給我聽,可是我就是不愛聽這些歌手──光良、梁靜茹等,真的不是我那杯茶。
我們在床上先聊天,這時他開始主動式地發問問題:你剛才去哪裡、你等一下去哪裡?休假你會去哪裡?
開門見山吧!為什麼像我媽一般地做問卷調查?
我只感到很厭悶。音樂不對味、問題不對位、房間不入格…
佑格真的太含蓄了,但他用一連串問題來打發我倆之間滯礙的冷場。他幾乎不敢用手去觸摸我,可是他在手機短訊裡卻如此張狂大膽。
后來,我直接問他,你還不採取主動?我就將手伸向他的T恤,然后作狀要除下了。
他說,「所以你現在採取主動了?」
所以,我們兩人就裸裎相對。他勝在年輕,他的肌膚煥發著青春的彈性,可是在歲月的渾然天成下,那是一幅幾乎快要崩塌的青春肉體,因為沒有經過塑造與鍛鍊。
他湊嘴過來與我接吻。我推拒不了。
然后我就聞到一陣異 味傳過來,隱隱約約,我整個人像僵硬了一樣,一直想避開這張嘴吧。但是他竟然咬住了我的嘴唇,從下唇到上唇,他的舌頭伸了過來攪拌著我的牙齦,我覺得自己 打開了一台沒有防腐設備的冰箱大門,一陣腐蝕性的寒意讓我全身發抖,我在掙扎著,然后他的頭就往我的身體探索了……
你寧愿用老二去應酬,總好過用口唇,我真的應該像《風月俏佳人》裡的Julia Roberts一樣,不該隨便獻吻。
未幾佑格問我:怎麼你硬不起來?
我望著我自己的老二,口腔裡的那股異味讓我過度震蕩,讓我全身由上至下都「失神」了,我呆了一陣子后說,「你需要大量地刺激我。」
「你要怎樣地刺激我?」佑格又問。
我想起了椰漿飯,他的擁吻讓我全身充血,他對我說,你要做一個優秀的kisser,你要伸出你的舌頭,與對方的舌頭打纏起來,他的舌頭伸過來時,我就忘我了,還有椰漿飯的手勢與撫觸,都讓我觸電…可是一切都不存在了…
我沒有答話。我不想告訴佑格,接吻就是我的情慾驅動器。
●
后來,我們一事無成。我們都DIY了。我就拿起他床頭的照片來看。還有聽著梁靜茹在哼哼唧唧地不知唱些什麼。
我后來就回家了,然后刷牙。我突然想起我剛才見到佑格牙齒上附有一些食物殘屑的畫面,所以更奮力地刷牙了。
佑格過后還是給我手機短訊,再詢問我們是否可以發展成情人。我說我們做朋友好了,沒有說明理由。
佑格再回短訊,他說他不明白為什麼,為什麼不少男生與他上床后,就沒有再發展的機會。他問我問題到底出在哪裡?
我不知如何告訴他,就是因為他的口氣不佳而致,而且我真的發覺自己需要乳牛來挑動我的慾望。
他說,他要知道是否問題出在他身上,他需要我的「評語」,讓他下次更進一步。
佑格一直發了手機短訊給我,在一個幾個小時的晚上,他已發了超過至少10則短訊給我,幾乎讓我難以招架。
天啊,我也是自己摸索竅門來學習,我總不成要給tutorial做性愛tutor吧!我赫然想起過去的經驗,有人愿意再見你第二次,證明你做對了一些讓對方歡愉的事情,否則只是bye,但不是再見了。
●
我們是否真的有太多的盲點,我還在學習著如何去發覺這些盲點,讓這些學習經驗成為日后的參考:
─在聊天室結識別人時,勿讓自己吹成一粒汽球,只在自我意識裡膨脹慾念,自己虛構對方的相貌外表,但最后可能一針就可以刺破這虛幻的夢想。
─寧愿與炮友口交也別接吻
─別讓自己成為沒有防腐的壞冰箱,那絕對會腐蝕致命的
台北第三章
誰可以告訴我,為什麼台灣的三溫暖稱為「會館」?
在大馬,「會館」指涉的是鄉親父老的聚集所,是血緣性組織的活動場所與基地,以宗親牌與鄉情來聯誼,然而在台灣的會館卻是沒有血緣性的人聚集的據點,是雄性肉食動物的「故鄉」,因為最終彼此的聯誼目的只是要性行為,或者是滿足性需求。
們是台灣的異鄉人,第一間到訪的三溫暖,就叫做彩虹會館。
彩虹會館據說是台北最當紅的三溫暖。彩虹這名堂已將同志場所的意涵呼之欲出襯托出來,這是俗套,也是一種直接的告白。
但更俗套的是,彩虹會館的裝設讓我們不禁挑了一下眉毛。
懷舊,還是過時?
滿地鋪滿了黑白相間的菱形設計氈子,你像走在棋盤上,需要步步為營來計算,但每個人都成為了棋子,你的身材就是你的籌碼。所以,我看到很多乳牛現身,帶著他們經過刻意鍛鍊出來的優渥本錢遊戈採花,但也成為別人的棋子而已。
然後我們看到幾個歐吉桑在接待處的沙發上吞雲吐霧,燈光慘淡,我還聽見絲絲台語言談和收音機的音樂傳入耳裡,十分「鄉土味」。而換衣間格是採用最原始的扣鎖頭設計,成本低,不必多費周章。
整體的初始感覺,就像搭了時光機,回到了六十年代的理髮室。你可以說這是復古與懷舊,但這也可以說是落伍與過時。
然後我們就更衣洗澡了。衝進洗澡間時,才發現這是開放式的設計,在半昧不清的黑暗中,每個人赤條條地走動──湊嘴到淨水器喝水、去泡JAGUZI、去蒸氣房與桑拿,還有去拉簾式的間格中沖涼,但仍在相當明亮的光線下勾勒出他們的形體。
與台灣老二說「嗨」!
這是我第一次見到如此多赤裸的男人,我當然要用目光與許多台灣老二打一聲招呼。他們對裸體的落落大方,絲毫不忸怩,讓我有些不自然,因為我成為現場中圍著毛巾而進行目光巡禮的異客。
在這天體浴場,我見到不少乳牛掠過眼前,當然還帶著一串串晃漾搖擺的下半身。
面對著不少昂胸壯碩的肌肉,下半身卻是萎靡不振的乳牛時,你是否會有生理反應?
但是,我只看到「具體」的陽具,沒有見到任何「巨體」。畢竟肌肉越是大塊發達的乳牛,若只是一般(或平均以下)長度的陽具,其實在視覺比例上是很吃虧的,因為長度這東西完對是相對性的,而未勃起的陽具甚至會像埋沒的尾指一樣。
然後我們就跑上樓去巡視了,那是一般的廂房與黑房設計格局,許多圍著毛巾的乳牛在走動著,他們可是帶著一幅健身後的成果來示眾的啊!還有不少看起來是以游泳等運動鍛造出來的身型,或許還包括阿兵哥呢?
我已血肉賁漲起來,因為我期待著一場「水乳交融」。
最簡陋、最原始的色慾祭壇
況且,在如此寬敞的廊道下,還配上相當明亮的照明燈,將每個人幾乎纖毫畢露地攤展下來,根本無法進行私密、隱匿性的「接觸」。
所以,我站在廊道時,看著不少乳牛浩浩蕩蕩地像走馬燈一樣繞著環形的廂房堆外走動,但是沒有人在我面前駐留。
後來,為了打發時間,我去端視每個房間的設計。大多數的房間都上鎖了,你無從知道到底裡面有何乾坤,到底是否有人在裡頭溫存?還是有人在裡頭黃梁一夢?
我瞧見一些空置的房裡的設備,那是一卷卷的廁紙零散堆放,沒有安全套供應器,但只有一張薄扁的床褥,配上凌亂不堪的翻掀床單,那不是繾綣的春夢痕跡,而是一片狼藉後的草草了事。
我抬頭,望見每個房門前都貼了號碼──從一數起,我數到38,共有38間廂房,供你進行最原始的肉慾儀式交流,這是38座色慾祭壇,這也是我頭一遭發現廂房貼號碼的三溫暖。
死寂的舞池
後來,我毫無斬獲,望著牆上的電子時鐘看板跳著格,我做了一小時的「遊魂野鬼」,我的眼前只是一夥夥流動飄移的心,我甚至沒有看到身邊有任何人去搭訕,或是被搭訕。
整個廊道只有貼著地氈的腳步聲,但是沒有人說話,除了一兩個是結伴而來的在竊竊私語,我甚至沒有聽到房裡傳出有何叫床聲,直至在入夜後只聽見斷斷續續的吟哦聲從角落端的一間廂房中傳出來──從聲音想像與描繪,那是不是一個被倒翻著身體,在一陣陣酣戰中用痛苦的叫聲來表達歡愉的吶喊?
後來,我走入了黑房。掀開了一層重甸甸的幕帘,我隱身在黑暗裡。用眼睛去熟悉暗沉下來的環境。
但是,我還是聽不到聲音,即使我佇足五分鐘後來觀察環境。儘管我知道週遭是站滿了人,這些幢幢人影在每每掀開幕帘時就無所遁形顯露出來,但是每個都成為木頭人,包括我自己。
我們一起在漆黑裡共同呼吸,我們感應到彼此的存在,只要一個伸手就可以撫摸到一具具肉身,但每個人還是不為所動。
這種感覺就像你在迪斯可裡跳下了舞池,可是那個舞池原來是沉寂無聲,每個人只是穩如泰山地站立著──那根本不是舞池。
沒有喘氣聲,沒有心跳聲,我不知道其他肉體是否與我一樣,心是熱的,但肉體是冷的,而且是慾望與自尊在交戰著──
我心裡暗想,怎麼台灣男生如此膽怯與被動呢?
後來直至凌晨二時許,我一直在轉念著如何與台灣的同志在三溫暖中搭訕,我想不到對白,我只聽見自己心裡的哀嘆。這時人潮已減退了,本來繞圈奔跑的乳牛更不復多見。
後來,我看到一隻乳牛佇立在暗廂外中打著呵欠,我瞟向他,他也不為所動,他寧愿自己一個人在寒冷的空調中打瞌睡,他也不愿望我一眼。
這時我已感到一股莫名的哀傷。我才想起自己是由內心地感到心力交瘁與疲憊,我反問自己:到底為什麼我要來台北呢?為什麼我來到這裡看到一隻隻乳牛招搖過市,到最後還望著一隻在黑暗中打呵欠的乳牛?為什麼我們需要兜圈子暗中求偶──只求一個擁吻、一趟觸撫,或是一次淫念的發洩而已?
後來,我就走下了二樓,回到更衣間格換起衣服就離開了。
這是一位讀者阿策(化名)寄給我的一封電郵,我沒有征求過他的同意,將內容發放出來:
「我在幾天前去見一個人,他是沒有照片的,只是知道他自稱有BF,兩個都是成熟年齡,受過高等教育,有經過常年鍛煉的美好身段,而且都是很開放的(你懂他們什麼意思了吧)。
然後我就去見其中一個叫H,他還沒有讓他的BF知道這正的東西,就好像是他來面試我看適不適合他,或他BF,或他們兩人,當時候我也沒有想那麼多,只是寂寞,就去見見H,其實我也沒有嘗試過3人行,我也沒有那麼大的決心去嘗試,我就想,可能我見到了他我會去嘗試吧!如果他真的有他所形容的那麼「美味」。
後來,我們見面了,他沒有說騙話,他的確是你所形容的那種「水牛」、成熟、開朗外觀,稍微黑銅色皮膚,穿著相當窄的有袖運動衣,而我……還穿著剛剛工作完畢然後趕去面試的工作襯衫。
他一見到我就說我絕對不是他BF的類型,我就問他如何判斷?他說他懂他BF的類型,然後我問他我是不是他類型,他說順其自然(當時候我還笨到不懂他意思)
然後我們就在嘛嘛檔喝茶,其實我看到他我是相當興奮的,他是我喜歡的那類型,我只知道他與他BF在一起10多年了,他說他的BF很好看,身材很漂亮,曾經拿過最佳身材10大,不過他們都是很保守的,不公開他們的身份。自從在兩個月前嘗試過第一次的三人行後,就開始很喜歡這種行為。
過後我問他,為什麼很多人都喜歡我的照片而不是我本人,而他竟然說是我的笑容問題,他說我不笑還好,一笑就因為我的牙齒而臉部走型,我那時候也不懂該說什麼,我還很幼稚以為他還對我有興趣,直到在車上,我嘗試摸他肚子(他還是有些肚腩),他就用手肘擋住了我的手,我就感覺很尷尬,後來他說他如果去 GAY BAR的話,有一班人在他面前他也不會選我,他說他要的類型是最好是黑黑的、身材很好,樣子中上而且有點壞壞的,我只是說「是嗎……?」
他載我去輕快鐵站,我自己搭車回去,那時候我突然覺得很傷心…我突然覺得原來是我笑的問題令到很多人不喜歡我,我不懂該怎麼辦,該拔掉我的虎牙嗎?還是整牙什麼的,我那時候突然覺悟,我是覺得沒有人會喜歡我的了,尤其是在這個圈子。
過後,我問很多人我的笑容問題,幾乎全部人都說沒有問題(除了某個自以為是的AH BENG PLU),還說我應該罵回那個侮辱我的人。
那時候我在想,是朋友騙我嗎?還是我自己騙自己?還是那個人的眼睛特別挑剔(尤其是有好看的男朋友的人),萬一如他說的,真的是因為我的笑容而趕走很多人呢?老實說,我自己看自己的確是沒有什麼問題,牙齒是走位沒有錯,但是沒有嚴重到臉步走位吧。(如果是走位的話那些牙醫還不快快把握賺錢的機會嗎?)
我都很煩惱了幾天,笑也不敢笑了,我實在是沒有借口去反駁H,因為他有好看的BF,我只有自己一個人,我能拿什麼來反駁呢?人不漂亮,就只有孤獨與被侮辱的份了。」
其實看到這封電郵後,我馬上就想給阿策回信了,因為第一個感覺是「哀傷」。可是,我覺得類似的問題不是阿策才面對的,我相信許多人會從阿策的信件找到共鳴和一些自己的影子,包括我自己曾遭遇過類似經歷,就像當面被人刮了一個耳光。
我沒有見過阿策,真的不知道他長成什麼樣子,不過重點真的不是他長成什麼樣子,而是阿策應該怎樣看待自己。
很明顯地,H用高姿勢來歧視、貶損他人,是因為他知道阿策對他神魂顛倒,他知道自己被人仰慕,所以就以稱臣他人的身段,踏人于腳底下──批評阿策的長相、炫耀自己的鑑賞品味。
我覺得像H這種人是同志圈中最可惡與可恥的獸性動物。
可恨的是,並不是有外形和有身材的同志會有這種擺款姿勢,而有些其貌不揚的傢伙也會犯上這種「暴發戶」的毛病, 為別人貼標籤扣帽子, 以他人的愛慕崇拜來當籌碼,然後用來撐高自己的EGO。
由于H的整體外形條件是符合阿策的口味,但是符合自己的條件要求,也不意味著需要去降低身份去迎合、刻意去改變自己。
不論燕瘦環肥,情人眼裡總會出西施吧,西施眼裡只有自己(這是李敖說的)。我們應該知道自己的長處在哪裡,而非注視自己的缺陷而已,這樣就陷入盲點了。
每個人總會有自己的niche market,自己的價值不是由別人來判斷高低多寡的,而是應該常常為自己加分。(當然不要一直加分加到101分,這應該是自負了吧!)
前幾天和白麗蝦談話起來提起華麗台播放著的《三個女仔一張床、這齣本地短片,我們談起裡頭有一隻很大隻的乳牛男主角(更糟糕的是我們都不知這隻牛是什麼名字,儘管他是一個名模),特別是他蒼白幼稚的演技,白麗蝦說:「上天真的很公平,那隻東西可以練得這樣大隻,可是整個人說起話來像白癡。」
的確,上天會公平地分配一些不同的資源給我們,所以我們也的確看到很多「智障水牛同志」,就像阿策所遇到的H一樣,得此失彼。
同志可以有尖銳的批判性,但沒有任何人有權利當面這樣去批評、對其他人說三道四,這種沒有口德的人,遲早會自己嚐苦果。
希望阿策能恢復燦爛的笑容,真、善、美應該是由心發出來,而非一堆皮肉堆砌而已,當然不要忘了繼續去約會其他男生,讓自己和別人一起探索與開拓自己。
ps:在此想起我寫過的一篇舊作:我是我主角
珍珍突然對我說,原來你的耳珠很厚唷。
然後我的耳珠就落在她的指尖裡拈了一下。我從心底裡突然間翻騰似地震顫了一陣。
那不是觸電的感覺,而是一種被侵犯的感覺。
是的,除了我的理髮師和母親以外,沒有人拈過我的耳珠,從小更沒有試過有老師拉著我的耳朵來斥責,因為我從來就是守規舉的學生。
可是珍珍這樣一個伸手,就觸撫了我的耳珠。「耳珠厚的人,很有福氣的。」她說。
我說,我聽說手掌多肉、溫厚而嫩軟的人,聽說更有福氣。珍珍有些不可置信,她在我面前攤開她的掌心研究著。
如果我是一個異性戀男子,我會趁機拉著她的掌心來看,然後觸撫著她的掌心說一些調情話,然後…
可是,我不是一個異性戀男子。我不為所動,珍珍就縮回她的手掌了。
●
我們是緊挨著,一起在Sushi King吃著迴轉壽司。老實說,這是我第一次去吃Sushi King。我一直覺得這種連鎖壽司店很不划算,東西少得可憐,但價錢貴得要命。
我都是在Cold Storage等那些超級市場買一盒50仙的壽司來咀嚼的。只是要解饞,只需要速戰速決,何必豪華貴氣?這不是我的速食法則嗎?
可是,因為珍珍說她要吃壽司來祭五臟廟,所以我被逼遵從。然後我們就找到了迴轉壽司前的位子,互挨著側邊來吃日本餐。
我們是要吃了壽司後,一起去看戲。她是名符其實的女孩,就是Sex and the City裡Carrie那種角色──時髦感,每次配搭衣服都會有煥然一新的感覺,在嬌嗲中說起話來就是有些大起大落,大是大非的那種。
後來我放眼望去迴轉壽司旁的座位,全都是成雙成對的年輕男女,親暱地挾著筷子聊著天,因為彼此都是一連串地坐在隔壁的感覺,所以會增添親近感。
我與珍珍也是如此,但我們不是情侶,我們更非姐妹淘,我們只是相識已久的工作夥伴。
但是,我們兩人在吃飯、看戲,這是一般情侶在做著的事情。
她坐直了身體,釋放出嫵媚的身體語言,我們的話題幾度落入冷場裡,因為她顯得不愿意談公事,反而談一些相當偏向于私生活的事情。
比如:「你與誰來談你的煩惱和心事?(我:朋友囉)誰呢?(我:喔,以前的舊同學)」、「你真的應該找一個人了…」、「唔,看起來你也蠻有錢的喔,因為你不必供車供屋子,又沒有什麼去購物花錢…」
我吃著壽司蘸上wasabi,一陣沖鼻的感覺轟上來,整個腦袋好像晃了一下,就像在腦袋裡燃放了一陣急速的炮仗,爆裂開來。我忍不住閉上眼睛,流下淚。
珍珍在旁邊吃吃地笑著,我沒有望著她,但我感到她的笑聲背後,有熱灼灼的眼神對望,我意識到那股熱能。
「啊,你真的不能吃辣啊!怎麼你這樣容易流淚呢?」她一直在觀察著我的表情。我不得不靦腆起來。但我不知道我是否有臉紅。我嘗試在掩藏著。
她說,「你再點多一些wasabi,以前我不高興吃壽司時就是點很多wasabi,然後就哭了出來。這樣會舒服一些。」
我在濺著淚,我怎麼沒有想到用wasabi來釋放自己的眼淚呢?
我想起,我沒有與椰漿飯來一起吃過壽司。我們沒有試過親近而又理直氣壯地在公眾場所一起用餐。我還以為sushi king是非回教徒食用的食肆。
我在拭著淚時,就沒有再蘸wasabi來吃壽司了。
●
可是,我現在是坐著一位多年的異性好友前面。她曾問過我是否是同志。我鄭重地作出否認。因為實在沒有必要對她pecah,我已體驗過一次向同事pecah後飽嚐的「惡果」。
我也知道她目前是單身情況,儘管她是一個動人的女生。
但,我還是第一次感覺到她的言談語調間的不同。
平時在公司裡大家談得非常投契,可是在坐在身旁時,她顯得有些矜持,有時會柔媚地在笑時拍拍我的肩膀。有時又有欲言還休的吞吐,特別是在我舉重若輕地推過感情生活問題時。
這不是以往我與她的溝通模式。絕對不是。我們是非常rigid和理性的談是論非,但不是這樣徘徊在調情,若有似無的語境中。
還有她伸手拈摸我耳珠的動作,這已逾越我的界線,那對我來說,是一個親密動作了。
為什麼會促成我們今晚的約會呢?
她在公司裡見到我時,問我為什麼看起來郁郁寡歡。我說:「因為寂寞,所以就這樣囉。」
珍珍就說,「你是時候找一個人來陪陪哪。」
「不如我找你好嗎?」我調戲般地回應,其他同事聽聞在竊笑著,然後她就爽快地答應晚上去看戲吃飯了。
●
後來,在看著迴轉壽司兜著圈子時,我也極力在兜圈,一直找話題來將飯局加溫。她對其他課題的反應顯得欲振乏力,很多時候只是冷擺著。
到最後我只有談回公事,這時我們已吃完了而感到饜飽,而不用一邊埋頭用餐一邊說話,我就將身子方向朝向她,可以與她對視說話了。
所以只有談公事。談我近來的工作狀況。吐了一桶桶的苦水。雖然我知道很掃興,可是我只有這樣打發我們一起渡過的時間。
珍珍有聆聽,不過她的反應看起來較好,至少有共鳴的人與事。
到後來由我付賬買單,我又覺得這是異性戀中男生應該做的事──男生要付賬的。即使珍珍也堅持應平分付賬,後來拗不過我的堅持,我就做了東。
戲上映前,我還陪她到一間服飾店逛了一個圈,跟著她的背後。然後看著其他女店員怎樣看著我們這一男一女。
不過她們沒有異樣的眼光,我反覺得心裡有一對異樣的眼光注視著自己:我反而覺得毛毛的。
●
我和珍珍就這樣看完了一齣戲,然後分手。
我的耳珠真的很厚嗎?我沒有在鏡子真正地研究過,不過我知道那是我的敏感地帶,那應該是一個充滿感官的薄嫩地域…
只有椰漿飯知道厚度。他會在前奏時含著我的耳珠,我會聽見他攪動舌頭的聲音,還有他在我背後包圍著我時,會咬著我的耳珠,就隨著節奏在喘氣著。一節又一節…
給一個女生摸了我的耳珠一下,我彷如失去了什麼,卻又喚醒了一些我內心世界的東西。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座斷背山。我突然想起了這句話。
Copyright © 2009 亞當的禁果, Powered by Blogger
CSS designed by Mohd Huzairy from MentariWorks
Blogger Templates created by Deluxe Templates